
1941年腊月的凌晨,掘港镇公所后院临时改成的刑场里,海风裹着霜气吹得枪口作响。行刑队刚端起步枪,被绑在木桩上的孙二虎猛地昂首,嘶吼一句“杀了我!”。这一声划破寂静,还未落地,旁边传来一句极不合时宜的“快给他松绑”,喊话者正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陶勇。惊愕写在所有人的脸上,毕竟两天前,正是孙二虎率人劫了新四军的军需船,伤了三个战士。

要理解陶勇这句看似荒唐的命令,得把时间线往前拨一年。1940年秋,黄桥大捷后,新四军东进如东,肩负开辟沿海通道的重任。彼时的近海,被五股大小海匪盘踞,日伪在陆上一堵,海面就靠这些人作梗。对外来船只而言,打着骷髅旗的孙二虎是“海上霸主”;但对如东百姓,他只是披着渔网的劫匪。陶勇要想把部队和根据地的生命线打通,这道关口躲不过,也绕不过。

有意思的是,孙二虎出道并不邪恶。十七岁孤身驾舢板闯黄海,靠力气和胆子养活一家老小。可是日军封港征税、伪警横征暴敛,他的渔获卖不出去,只能掉头抢商船维生。“活命要紧”成了口头禅,慢慢把他推向匪道。短短两年,他手下聚了百余人,五条三桅大船火力不逊一个排。大洋深处,孙二虎认枪不认旗,谁肥他抢谁,新四军也未能幸免。
1941年初,新四军两次运输受阻,陶勇坐不住了。直接围剿?掘港外那片暗礁密布的水域,新四军不熟;拖延不理?根据地物资断顿。陶勇反复掂量,定下一招“擒其魁,化其众”。侦察排化装渔民潜入庙会,十七人潜伏三处,连夜摸清岗哨和撤退路线。农历八月十二的龙王庙会,人声鼎沸,孙二虎带着七名心腹进庙吃素斋,门一栓,早布好的暗枪齐亮。短促交火后三分钟,“海贼王”被拿下。

被俘第一夜,陶勇没有审讯,只让医护给孙二虎处理臂上的擦伤,还递了碗热粥。第二天开审,孙二虎一句“老子活够了,痛快点”吼得队列一震。陶勇却笑了,他看中的正是这股不服天不服地的狠劲。枪毙一个匪首容易,可苏中缺的不是烈士,而是熟水性懂航道的敢死队。陶勇示意解开绳索,转身对警卫员说:“带他去洗把脸,回来谈事。”
短暂的几小时里,陶勇给孙二虎摆出三笔账。第一笔是仇账——三名负伤的新四军战士,弹孔还在;第二笔是苦账——五千多名难民眼下靠根据地救济,海上物资一断,就是断粮;第三笔是前程账——“你枪法好、懂船,会游弋暗礁,跟着我打鬼子,兄弟都有活路。”话音不扬,却字字击在要害。孙二虎低头沉默,半晌冒出一句:“我若反悔呢?”陶勇抬手在腰间拔出那支缴获的驳壳枪,放桌上:“枪还你,路你挑,天亮前给我答复。”说罢转身离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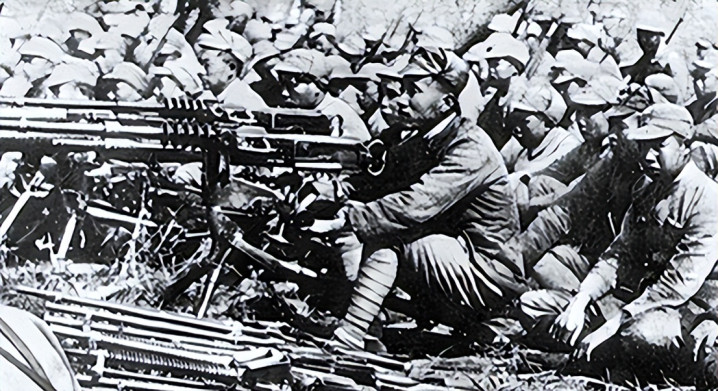
午夜两点,卫兵禀报:孙二虎坐在屋檐下,枪放膝边,没跑。“旅长,他说等你。”陶勇走过去。月色里,孙二虎站起,举枪倒扣双手奉上,“我改,条条都记心里。”陶勇只是点头,没多言,挥手让人登记番号:特别水上侦察大队。此后两周,整训、分枪、立规矩,连夜完成。纪律条文写得极硬,“扰民者枪毙”赫然在首条。孙二虎盯着那行字,咂嘴,却没吭声。
收编容易,改性难。三个月后,几名旧部偷偷带酒上船,醉后闹事,被地方告到旅部。陶勇罚了责任人十天禁闭,还扣了孙二虎三个月津贴。酒一醒,孙二虎跑去理论:“兄弟们跟着我多年,不容情面?”陶勇反问一句:“你要面子还是要队伍?”冷场三秒,孙二虎自认理亏,回头把闹事的人押到旅部,请自家鞭子执行五十军棍。第二天早操,全队列队,他亲自宣读新四军纪律,声音嘶哑,却无人插科打诨。从那刻起,水上侦察大队才算真正“脱胎换骨”。

1943年春,日军对苏中发动清乡,大队奉命护送两船药盐穿越封锁线。夜里薄雾,鬼子炮艇突然逼近。孙二虎带三条小船诱敌,借暗礁反打,一发穿甲弹直中敌艇油舱,火光冲天。两船军需安全抵岸,药盐救下数百名伤员。战后总结会上,陈毅看着战报,抬眼笑问粟裕:“这‘海贼王’如今如何?”粟裕答:“已成我军水上尖刀,可放心用。”

战火终结后,孙二虎改名孙仲明,军籍编号留在档案,职务写着“华中野战军水上侦察营营长”。有人问起当年的松绑,他只说一句:“陶旅长救的不是我,是那些等着物资的前线弟兄。”短短一句,概括了那桩看似匪夷所思的决定背后的深意:枪毙一个人容易,改造一支队伍、打通一条生命线,更难、更值。
配资服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